心理疾病-进食障碍的治疗方法
发表于 2022-11-13 13:31
心理导读:尽管进食障碍相对不常见,但进食障碍仍然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广大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戴安娜王妃最近在《王冠》中描写自己与贪食症的斗争的故事再次将进食障碍带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这篇简短的评论将检视和进食障碍有关的最新发现,包括进食障碍的诊断、流行病学、神经生物学和治疗。 ---www.psy898.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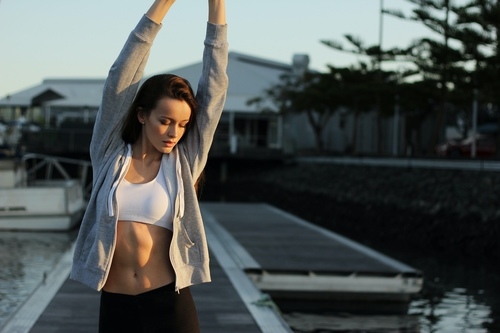
进食障碍的治疗方法
八年前,DSM-5对进食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了重大更改。DSM-IV标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只确定了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这两种进食障碍。因此,许多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都获得了非特异性进食障碍诊断(eating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EDNOS)的标签,该标签没有提供和患者困难性质相关的信息。
DSM-5以多种方式解决了此问题(详见DSM-5喂食和进食障碍列表)。对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诊断标准略有扩展,以便每个类别涵盖更多的患者。但是,另外两个更改对减少非特异性诊断的使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喂食与进食障碍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
异食癖 Pica
反刍障碍 Rumination Disorder
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 Avoidant/Restrictive Food Intake Disorder
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
神经性贪食症 bulimia nervosa
暴食障碍 Binge-Eating Disorder
其他特定的喂食和饮食失调症 Other Specified Feeding or Eating Disorder
未特定的喂食和饮食失调症Unspecified Feeding or Eating Disorder
首先,是暴食症(binge eating disorder,BED)的添加,此前在DSM-IV的附录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暴食症是美国最常见的进食障碍症,因此其在DSM-5中的正式认可导致对非特定诊断的需求大大减少。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将DSM-IV中的“婴儿或幼儿的喂食和进食障碍”的部分与“进食障碍”相结合,形成了扩大版的“喂食和进食障碍”。因此,此更改包括三个诊断类别:异食癖,反刍症和婴儿期或幼儿期进食障碍。异食和反刍障碍很少被诊断。
临床中很少使用婴儿或幼儿早期进食障碍这类诊断,并且自从将其纳入DSM-IV以来几乎没有被研究过。负责评审DSM-5进食障碍标准的进食障碍工作组意识到,有很多人严格限制食物摄入,但没有神经性厌食症,这其中许多是儿童。例如,进食后剧烈呕吐后,一些人试图通过不再进食来预防复发,从而导致潜在的严重营养紊乱。DSM-IV没有针对此类个体的诊断类别。因此,DSM5扩展了DSM-IV中的婴儿或幼儿早期进食障碍的类别,并更名为“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ARFID)。综合起来,这些变化导致了对进食障碍的非特异性诊断类别的需求大大减少。
在评估饮食异常诊断标准的建议变化的影响过程中,进食障碍工作组意识到另一组正在临床治疗个案的症状与现有或提议的类别都不完全相符。这些都是个案,其中的许很多人以前就已超重或肥胖,他们已经减轻了很多体重,并出现了许多神经性厌食症的症状和体征。然而,在介绍情况时,他们体重的维持在正常范围内或之上,因此不满足神经性厌食症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工作组建议,用DSM-5替代DSM-IV的非特异性进食障碍诊断时包含对此类人员的简短描述,即,“其他特定的喂食和饮食失调症”(OSFED);该描述被标记为非典型神经性厌食症。非典型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症状、并发症和病程与典型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相似,程度上的不同仍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进食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
尽管进食障碍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但相对来说还是很罕见的。Tomomo Udo博士和Carlos M.Grillo博士于2018年9月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对来自全国超过36,000名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了调查,该项研究在2012-2013年期间使用了非公开诊断性访谈。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BED)12个月内的患病率估计分别为0.05%,0.14%和0.44%。尽管这些疾病的相对发病率与先前研究中描述的相对发病率相似,但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绝对的估计值会略低一些。进食障碍、尤其是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在女性中更为普遍(尽管男性也受到影响)。尽管在所有种族和族裔中都出现进食障碍,但非西班牙裔和西班牙裔黑人受访者中的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例要少于非西班牙裔白人受访者。与长期的临床印象一致,终生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收入较高。
最后,在考虑暴食障碍(BED)在DSM-5中正式获得官方认可时,一些批评者建议,由于几乎每个人偶尔都吃得过饱,BED就是DSM病理化正常行为的误导性例子。Udo和Grilo的研究报告指出BED的患病率较低,经过仔细评估,BED仅影响少数人,因此与正常情况不同。
进食障碍的发生率(incidence,每年新发病例的数量)是否正在增加,是一个有争议和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话题。一些研究(例如Udo和Grilo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进食障碍的终生发生率低于年轻人,这表明进食障碍的发生率可能正在增加。但是,这也可能反映了最近对进食障碍的认识和知识。其他研究对相同环境中的进食障碍频率进行多次检查,随时间的推移,似乎表明神经性厌食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发生率大致保持稳定,而神经性贪食症的发生率却有所下降。想必,这反映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例如对超重的接受度提高,以及与不当补偿措施(如暴饮暴食后自我诱发呕吐)相关的压力降低。
COVID-19大流行几乎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生活,并造成了严重的财务负担,医疗和心理压力。初步研究表明,这种压力加剧了先前存在进食障碍症的人的症状,并导致普通人群暴饮暴食的增加。希望这些趋势将随着大流行的成功控制而得到改善。
进食障碍的神经生物学解释
和进食障碍的发展以及持续性的潜在机制的最新研究集中在奖励和非奖励/惩罚性刺激的处理上。几项研究表明,神经性厌食症的人较难区分在不同概率之间获得奖励的刺激量。其他研究表明,当在MRI扫描过程中查看食物图像时,神经性厌食症的大脑奖赏区域往往比对照组少。这种缺陷可能与已知参与奖励处理的大脑区域中的多巴胺功能紊乱有关。基于新兴的计算精神病学方法的研究表明,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对于从惩罚中学习可能尤为敏感。例如,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刺激可以导致奖励金额减少。可以想象,他们可能知道吃高脂食物可以防止体重减轻,不良体重增加,因此他们开始避免食用这种食物。这些研究以及其他一系列研究集中于探索基本的脑机制,以及它们在神经性厌食症中如何遭到破坏。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面临的挑战是确定这种机制中的紊乱与神经性厌食症的饮食紊乱特征究竟有何关系。
近期的一些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研究,着眼于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在决定吃什么食物时做出持续适应不良选择背后的神经回路。此类研究成功地捕获了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完全避免食用高脂食品的事实,并已证明,与健康个体相比,此类个体在决定饮食选择时会利用不同的神经回路。这些结果与以下的观点一致:许多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持续存在一种可能归因于,他们围绕食物选择时,建立了一种自动化的、刻板的和习惯性的行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所面临的挑战是,确定这些适应不良模式是如何迅速发展的,又如何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
神经性贪食症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大致相似。尽管结果复杂,但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似乎发现食物刺激的奖赏更高,并且有迹象表明对甜味的奖励响应性受到干扰。一些研究使用Stroop任务等行为范式评估了冲动控制障碍。(Stroop任务会向个人显示一个命名以命名颜色的单词(例如,“红色”),但要求其命名拼写该单词的字母的颜色例如,字母red为绿色)。在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个体中,执行此类任务的难度不断增加,并与前额叶皮质厚度减少有关。
进食障碍的遗传学解释
人们早就知道进食障碍往往在家庭中发生,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部分反映了个体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很明显,罹患最复杂的人类疾病(包括肥胖症,高血压和进食障碍)的风险与许多基因有关,其中每一个基因对风险的影响均很小。由于单个基因的贡献非常小,因此需要检查来自大量患有和不患有该疾病的个体的DNA。例如,精神分裂症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已检查了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00,000多个对照者,并确定了100多个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基因位点。
GWAS正在研究进食障碍的遗传风险,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于神经性厌食症。精神遗传学协会已收集了10,000至20,000名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和超过50,000名对照者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已确定了8个导致神经性厌食症遗传风险的基因位点。此外,这项工作还确定了神经性厌食症与一系列其他已知与神经性厌食症共病的疾病(如焦虑症)之间的遗传相关性,以及与肥胖的负遗传相关性。这些数据表明,神经性厌食症的遗传风险是基于与一系列心理和代谢/人体测量学特征相关的基因座(locus)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进食障碍的治疗
尽管我们对如何最好地治疗进食障碍患者的认识没有显著发展,但近年来有了一些重要而有用的进展。
对于神经性厌食症,可以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治疗方面最重要的进步是青少年的家庭治疗。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Maudsley方法(Maudsley method,译注:英国伦敦Maudsley医院的Dare和Eisler开发了的特殊的基于家庭治疗的FBT)。在治疗师的指导下,家庭成为了改变的主要主要机构,并负责确保饮食行为正常化和体重增加。这种方法与以前的治疗策略明显不同,以前的治疗策略假定父母的参与不会有帮助甚至有害。现在,广泛认为以家庭为基础的治疗是神经性厌食症青少年的首选治疗方法,并且已经适用于治疗神经性贪食症。
对于父母来说,以家庭为基础的治疗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要求整个家庭参于治疗,在治疗的一个早期阶段中要进行一次家庭用餐,在此期间,父母要承担说服青少年食用比自己预期更多食物的艰巨任务。最近在一些研究中探索了一种替代但相关的模型,称为“以父母为中心的治疗(parent-focused treatment)”。通过这种方法,父母会与未患病的青少年或家庭其他成员的治疗师会面,并且接受指导,了解如何帮助青少年通过与传统的基于家庭的治疗方法几乎相同的技术来改变其行为。几项小型研究已经检验了这种方法,结果表明了(和Maudsley方法)类似的有效性。尽管这需要更多的研究,
COVID-19大流行导致远程提供精神科护理(包括基于家庭的治疗)的戏剧性加速。尽管通过视频会议提供基于家庭的治疗的工作在COVID-19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因为这种特殊形式的护理尚不广泛,而通过符合医疗电子交换法案(HIPAA)的视频链接提供这种护理的可访问性将会大大增加。几项小型研究表明,远程提供基于家庭的治疗是可行的,并且可能是有效的。COVID-19对面对面接触的限制加速了远程家庭治疗的实施;希望新的研究能证明它的有效性。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与能够直接测量体重和监督患者身体状况的医疗专业人员进行地面接触。
神经性厌食症的成人治疗通常在十几岁时就已发展出了这种疾病,并且已经患病5年或更长时间,其治疗仍然具有挑战性。结构化的行为干预措施,例如专门住在医院的患者,日间计划或住宿中心提供的干预措施,通常会导致体重显著恢复以及心理和生理状况的改善。但是,急性护理后的复发率仍然很高。此外,大多数成年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构化方案的治疗。最近的一项有益进展是,奥氮平(剂量为5mg~10mg /天)对成人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体重增加有中等帮助,并且几乎没有明显的副作用。遗憾的是,它不能解决核心的心理症状,必须被视为辅助标准护理。
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患者的治疗的研究进展不多。对于神经性贪食症,认知行为疗法仍然是心理治疗的主要手段,SSRIs仍然是首选药物。对于暴食症,多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与暴饮暴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2015年,FDA批准了针对暴食症个体使用的兴奋剂lisdexamfetamine(Vyvanse)甲磺酸利地美胶囊。与大多数心理治疗不同,甲磺酸利地美胶囊与中等程度的体重减轻有关,但对脉搏和血压的影响可能值得关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进食障碍患者的新型心理治疗方法的开发和应用。这些包括辩证行为疗法(DBT),接受和承诺疗法(ACT)以及整合认知情感疗法(ICAT)。尽管只有少数对照研究检验了这些疗法的有效性,但传闻信息和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可能是更成熟干预措施的有用替代方法。
结语
尽管进食障碍仍然不常见,但是临床上的重要问题是以喂食或进食障碍相关行为的持续紊乱。前沿的研究集中在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上,它采用了新颖且发展迅速的方法。在治疗方法方面取得了适度的进步,包括COVID-19大流行通过视频链接加速了治疗的实施。未来的研究有望阐明ARFID和非典型性神经性厌食症的性质,并导致开发出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尤其是针对长期进食障碍的个体。
(作者/Timothy Walsh 文 | 编译/mints | 来源/心理学空间)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理氧吧”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22 psy898 All Rights Reserved










